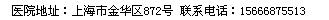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神经性厌食 > 厌食症状 > 狗事儿
狗事儿
文/绒绒
我记不清家里养过多少只狗。
从小我就特别崇拜我妈。只要她一敲盆子,无论那个盆子里有没有狗食,无论那个敲盆子的棒子是从哪找来的一根快腐朽的破木棍,家里的狗还有街道边流浪的猫猫狗狗,一窝蜂地跑过来吃。
我觉得我妈像一个将军,挥舞着棒子,把多吃多占的赶走。
而我们家在每一个不同的阶段养的狗,无论是小白、小宝还是格格,它们都等着我妈把已经吃饱的流浪狗赶走以后,再扭捏着、低眉顺眼地走过来,把头埋在盆子里大块朵颐起来。
我们家好像就没养过一只有骨气的狗。
在镇子里一群的家狗野狗中,它们都是垂头丧气走在队伍的最后边的那一只。它们的叫声好像比别的狗小,每次打架回来都是被揍的那一个。
只有一只很特别,我给它起名叫小黑。
小黑有一身乌黑发亮的毛,瘦瘦小小,牙齿略有畸形,俗称地包天。它长得没有以前我们家养的狗漂亮,叫的时候低沉呜咽,像个小老头儿在咳嗽。
我却格外喜欢它。
我用火柴盒给它做鞋子,小黑走起路来发出“哒哒哒”的声音。小黑很不开心,轻轻甩了几下,火柴盒就被甩到了一边。
我把我妈的裙子套在它的腰上。小黑掉毛,一把一把的掉,翠绿色的裙子上全是黑色的狗毛。我妈回来,用鞋底子把小黑打出门外。
小镇上的狗都是用来看家护院的,小黑也是。
后来等小黑长大了一些,掉毛越来越严重,地包天也越包越严重,随便摆出一个表情都是龇牙咧嘴的,我妈就不让它在屋子里住了。我和我爸一起在房子门前用砖头给它砌了一个窝。狗窝与大门口之间的院子上空连起一根铁丝,那是妈妈用来晒衣服的。
不晒衣服的时候,我们把小黑的铁链就栓到铁丝上。
小黑顺着铁丝,从狗窝跑到大门口,再从大门口跑回狗窝,龇着它好像永远合不上的牙齿。威风极了。
过了一年,也许是两年,小黑得病了,厌食症。
它不吃饭,无论我妈把盆子敲得多响,盆子里的饭菜有多香,小黑都不吃饭。它一天一天变瘦,一天一天变懒。
我踩着一把凳子,把它的链子高高地挂在晒衣服的铁丝上。
我说:小黑,你跑啊!
它匍匐在地上,有气无力地看了我一眼,闭即闭上眼睛。
我永远都记着和小黑分别的那一天。
那是一个夏天,我穿着一条墨绿色的裙子,上衣穿什么我忘记了。中午的时候,有人给我爸打了一个电话,我爸唉声叹气半天,随即让我把小黑牵到一个亲戚家里。
我牵住拴小黑的铁链,从我家到他家,小黑犯懒不爱走路,走一会儿歇一会儿,好像走了很久。
我走得汗流浃背,小黑一直吐着舌头。人家说狗是不会流汗的,狗热的时候就把舌头抻得很长很长。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和小黑,那一天都是满身大汗地走完了那一段路程。
走到之后,亲戚家的姐姐问我:困不困?
我晒得满脸通红,姐姐给我喝一大瓢凉水。头上的太阳晒到我的脸上,我感觉脸快晒炸了。我点点头。
醒了以后,我感觉世界都坍塌了。
透过窗子望出去,乌黑发亮的毛散落一地,院子里散发着腥臭的味道。小黑活了两年,就和这个世界永远告别了。
能证明它曾经存在的证据,也许只剩下隔壁房间一桌残羹剩饭里的狗肉和院子里那一摊被艳阳晒得发臭的内脏。
姐姐见我醒了,从柜子里掏出一个手钏,很多蓝色的珠子被一条皮筋穿着。姐姐一下把它戴到我的手腕上。
我记得她说:这是从云南带回来的,可贵了。
我不再敢看院子,低头把手链退下来,放到腿上。
它一点也不好看,它和我墨绿色的裙子一点也不般配。
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它们要用这么残忍的方式对待我的小黑。我不懂得反抗,不敢发脾气,我甚至不敢告诉大人们:你们把我唯一的朋友吃了,我很伤心。
在很多年以后,我回忆起当年看见那具连尸体(抱歉,那甚至谈不上是一具尸体)时,我连眼泪也没流一滴。
不是我不爱它,也不是我多心狠,只是我还不明白这个世界。我也不懂得,既然没能力保护,就不应该去占有。
长大了以后,我还会经常想起小黑。
我妈说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像猪一样,记吃不记打。所以我记得的,大多是与小黑快乐的时光,我们一起沿着一根上了锈的铁丝奔跑,一起玩过家家,我反复地跟小黑说话,那时候我感觉它可以听得懂。
我的自我保护程序,常常让我屏蔽掉我的痛苦,让我忘记我是如何成为伤害小黑的帮凶的。所以很多年以后,我又养了一只狗。
其实养呼呼,也是因为一句非常随意的玩笑话。
大概是年,我到济南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在单位附近租了间一居室的房子。单位有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太,论资排辈也属于公司的元老人物了,所以单位里从上到下都比较尊重她。她养了个串儿,狗爹是京巴,狗妈是蝴蝶犬。我还有个刚毕业的女同事,长着一米七五的大个子,管自己叫田螺小姐。
有一次大家围在一起吃午饭的时候,田螺说想养一只狗。老太太说,我送你一只。我当时顺嘴说了一句,我也想养。
就因为这一句似是而非的玩笑话,我的生命里迎来了一只叫做呼呼的小狗。
它是在一个秋天的午后来到我家的。
老太太给我打电话,说要送给我一个礼物。我心里一惊,完全忘了自己曾在大块朵颐时说的那一句玩笑话。
我立刻出门,坐了11站32路车去迎接我的那一份礼物。
见到呼呼的一瞬间,我的心快被融化了。它是只才出生不久的比熊,被老太太放在一只狗篮子里,铺着暖融融的小被子。
它就躺在被子里面,紧闭着眼睛,刚吃完奶,嘴角留着白色的泡沫。睡觉的时候发出“呼噜噜”的声音。
我问老太太,它叫什么呀?
老太太说,你喜欢叫它什么,它就叫什么。
我捧过狗篮子:就叫它呼呼吧。
呼呼跟我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老太太跟我说,刚出生不久的小奶狗,一般每天要喂三到四次。我按照她的吩咐给呼呼买了两包酸奶,用针管一次给它喂上一点儿。
喂了几次以后,我发现呼呼最喜欢君乐宝的橙味儿酸奶,给它喂这种酸奶的时候,它吃得最起劲儿。
第一个周末,呼呼和我“你尿床来我铲屎”,过得算是相安无事。可是到了周日的晚上,我发现我搞不定了。
呼呼因为太小,所以间歇性失眠。一失眠就乱叫,可能这一次叫因为饿了,喂了点酸奶以后安静片刻,过了一会儿又叫起来。
一会儿喂奶一会儿铲屎,搞得我一晚上也睡不安生。
呼呼每一次都叫得撕心裂肺,加上我住的房子隔音差点儿,半夜邻居来敲我的门,让我管好自己的狗。
好在当时我住的地方离单位近,只有一站路。一个来回只需要10分钟的时间。呼呼来的前几天,我几乎每天中午都跑步回家,给它喂一些吃的,把它拉过的地方打扫一遍,再陪它安静地呆一会儿。
呼呼当时连站都站不稳,在我的身边颤悠悠地迈着几只小腿,四肢极不协调。地板太滑,它走了没两步,“叭叽”一声把整个身子都呼到地上。
我把它抱起来,放回篮子里,走到门跟前,看它一眼,把门锁好。
呼呼跟我一起生活了极为短暂的一段时间,二十几天,或者一个月。
我甚至没有经历过和呼呼一同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在草地里奔跑。或是它一颠一颠地紧紧跟在我的身边,我要很小心很谨慎地走路,因为怕一不小心踩到了它的脚。
自始至终,我非常不愿意承认,我是因为碍于老太太的面子,所以不敢拒绝她,不敢说:这只狗我不可以养。
我没有准备好,我没有与它生活一辈子的勇气和决心。无论它健康还是疾病,无论它年幼还是年长,我都与它一起悦尽人间百态,尝尽风霜雪雨。从人生的某一个起点,到其中一个生命的终结。
最后我把它送人了。
因为呼呼来了以后,我没睡过一个好觉。我每天晚上都要起来两次或三次,给它喂食,给它擦尿铲屎。
慢慢地,我开始精神衰弱,每天上班的时候都感觉头重脚轻。
对于我来说,呼呼变成一只拖累我的宠物,我还要工作,我还要生存,我分身乏术没办法很好地照顾它。
而对于呼呼来说,我是它生命中的唯一。它没有我不行。
这太不公平了。
我把它送给一个住平房的朋友。他说他家里有一个院子,家里有一只体型庞大的狗,跟它比起来,呼呼也许只是个芝麻。
我猜呼呼在朋友那里应该会生活很好,因为能把一只狗养成那么庞大的话,应该已经有了足够的勇气和决心吧。
送走呼呼那天,朋友骑着摩托来我家。
我把狗篮子交到他手里,他接过去的时候,呼呼还在里面呼呼大睡。不知道一醒来它会不会有这样的感慨:呀,那个女的怎么变成男的了?
或者,在呼呼的世界里,没有这个女的和那个男的之分,只有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之别吧。
我问朋友:你能好好照顾呼呼吗?
朋友一笑:呼呼太难听了,我给它重新起个名字吧!
我一下就哭了。
我愿意相信我的这个朋友一定把呼呼照顾得很好。
我一直都没有再过问,呼呼是不是长大了,它有没有变成一个十分可爱的模样?
我想知道它过得怎么样,却怕听到不好的消息。我放弃了它,所以我怕听到不好的消息。
后来我不断地回忆,不断地想起。
我想如果可以回到当初,我一定不会把呼呼从老太太手里接过来,让它有一次颠沛流离的不好经历。
如果可以回到当初,我一定在小黑通往地狱的途中放开那个铁链,把它留在某一个街角,让它自由地生活,让它变成一只流浪狗。
然后在某一天的黄昏,我拎着一根精致的小木棍,节奏错落地敲起一只盛满饭食的盆子,小黑欢快地跑过来,冲我摇尾巴。
我蹲下去,抚摸着它的头,说:乖。
抱歉,这篇文章可能让你难过了。我在朋友圈里说,我要写一个小动物的系列,为我的猫猫狗狗情结,做一个纪念。
我也没想到,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搜罗出的竟然是这些记忆。这是第一期,也许还会有第二期、第三期。
也许不会再有了。
我从来都没有亲口对它们说的话,我想在这里说一声:
对不起,小黑
对不起,呼呼
绒绒,写于年12月9日
------------------------